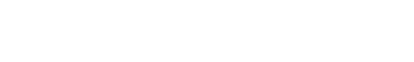对一个心智还不成熟的高中生来说,老师、家长的表扬与肯定,简直像ICU的强心剂一样有起死回生之效,而批评或忽略,也颇有拔管断气之虞。很多天资聪颖的同学,成绩或上或下或高或低的原因或在于此,好像大家是为老师、为学校而读书似的。
记得刚到震泽中学,教物理的张国元老师担任我们班的班主任。摸底考试,我得了100分,其中一道力学题,我把示意图画到试卷反面,占满了一张A4纸。张老师阅卷时大喜,常拿此事教育其他同学。张老师是震泽本地人,家住学校河对面的小弄堂。听镇上的女同学说,张老师妻子非常美,像一位电影明星,我们几个唐突的女生便在晚饭时分跑去他家门口围观,结果张老师拿出家里长凳子小椅子招呼我们就座。
隔壁班的女同学沈红梅,英语和数学成绩拔尖,我一直羡慕她天赋好,但她告诉我,她来震泽中学前数学并不好。一次考试,班主任李金根老师偶然表扬了她,她大为感动,内心暗暗发誓,谁对她好,她就好好上谁的课。红梅说,李老师看到戴力行先生早读课“每日一诗”,唯恐自己班的学生落后于人,竟凭一己之力,开启数学老师教语文的模式,给学生抄写名言佳句。
高三时,陈蓉初老师教我们物理。陈老师声音又高又尖,讲课条理清晰、妙趣横生。可是他眼睛一瞪,我脑海里总浮现出张国元老师和蔼可亲的样子,甚至不想做陈老师布置的作业。陈老师偶尔笑眯眯夸我有进步,又让我受宠若惊,顿时喜笑颜开。
1982年高考一结束,从校长到班主任,从主课老师到体育老师,似乎人人摩拳擦掌,个个不眠不休,逐个找我们核对答案、预估分数,为大家量身打造高报方案,冲刺全国第一流重点大学。填报志愿的时候,马铁枢校长更是具体落实到谁报考清华大学、谁报考北京大学、谁报考中国人民大学、谁报考复旦大学、谁报考南京大学等,确保全国顶尖大学都有震泽中学的学子。那个年代的学生及家长,对学校报以无限信任,家长甚至觉得把孩子交给学校比交给自己还放心;二来,家长自认农民工人出生,没有什么见识,几乎是感激涕零地视学校的建议为最好的安排。
果然,1982年震泽中学捷报频传,150名同学中,70%的同学达到了录取分数线,其中一半是重点大学分数线。马校长运筹帷幄、苦心积虑规划的十几名同学,几乎都考上了理想中的北大清华复旦人大,还有七八名同学被保送了南京大学。这一年的震泽中学,几乎是一战成名。建校59周年的震泽中学,一身荣光。
夏丏尊先生在翻译《爱的教育》时,说过这样一段话,“教育之没有情感,没有爱,如同池塘没有水一样。没有水,就不成其池塘,没有爱就没有教育”。震泽中学的老师们,用他们的爱心与知识、汗水与时间,甚至健康与生命,担当起了“爱的教育”四个字。
学校在1982年的高考中创造辉煌,而顽劣骄傲的我马失前蹄,自以为得心应手的作文意外失分。高考前,马校长征求我意见,保送我上南京大学的古汉语文学专业。我在无知中婉拒了,辜负了马校长和老师们的厚爱。
1983年我改考文科,“高四”班主任、语文老师詹希儒先生千叮咛万嘱咐,谨慎审题,作文宁可平庸一点,不可追求“语不惊人死不休”。时年我高考总分509分,语文90多分。马校长给我定的目标是冲刺复旦大学新闻系。遗憾的是,我的高考分数过了复旦大学的分数线,却没有过新闻专业的门槛,最终与复旦失之交臂。
几经辗转,我被詹希儒老师的母校录取,专业是首次引进中国的旅游经济管理。彼时刚刚改革开放,国家亟须对外交流服务人才。我听了詹老师一半话。时光荏苒,我离开旅游行业,改换门庭进了媒体单位。
作为一名震泽中学的高中毕业生,1979年入学时,我带着吴江中考第一名的光环,收获了各科老师的偏爱。1981的作文获奖,震泽中学又给了我人生中的最高光时刻。也许应了张爱玲所说的“成名要趁早”,几十年后师生相聚,毛福源校长还要提起往事,不吝给予我最大的赞美,使我十分惭愧。值震泽中学百年校庆之际,写下此文,献给母校所有的老师和同学,遥寄我对母校的不尽深情。
(吴丽琴,震泽中学1982届毕业生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