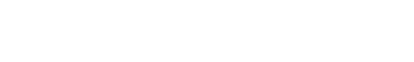有人说,少年是一个人最美好的时光。
1957年秋,我这个又瘦又黑的农村少年走进了震泽中学的大门,从此,我与震泽中学结缘,度过了从初中到高中的六个春秋。这六年的学习和生活,使我从一个懵懂无知的农村孩子成长为一名高中毕业生,还顺利考入了全国外语最高学府——北京外国语学院(今天的北京外国语大学),这与老师们的辛勤教学是分不开的。
震泽中学的老师不但学问好,对学生的关心也是无微不至。每天早晚自习课,总有老师在你身边走动,如果你有问题可以随时得到解答。他们也是“上有老,下有小”,但他们做工作从来不懈怠。沈蕴真老师由于家庭变故,一个人带着一双儿女生活。那时她工资微薄,经济上真是捉襟见肘,但她从来没有喊过苦,从来都是兢兢业业,守护着每一个学生。其他老师工资收入也不高,但他们还是尽力帮助因困难而面临辍学的同学。
我们同学一提起母校,几乎都要说到一个人:马教导马铁枢。他像一位管家一样管理着学校的教学和日常事务,用现在的话说,马教导就是一名CEO。他总是第一个到办公室,最后一个离开。他每天把教学安排写在办公楼前的黑板上,各年级各门课程的进展,乃至每位老师的身体状况他都了然于心。上世纪80年代,我因为偶然的机会回到母校,马教导见了我真是喜出望外。为了鼓励学生学好外语,他还把几个班的学生集中起来,让我给他们讲学外语的体会。原本心里有点发怵的我,在马教导的鼓励下讲了一节课。那天讲到母校对我的培育之恩,我话语哽咽、眼里噙着泪水。
母校对同学们的课余爱好总是很支持的。记得学校还举行过一次书法比赛,我练了柳公权的玄秘塔碑,还得了个一等奖。我的信心更足了,报名参加了学生会黑板报“震中园地”编辑和书写员的招聘,还被选上了。就这样,我为这份“校刊”工作了六年,也算是“老资格”的“媒体人”了。我这点“雕虫小技”在日后的工作和学习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,甚至到了使馆文化处,这些技能还派上了大用场。写写画画是手到擒来,没有人敢说“文化处的人没文化”。
小时候,我的一个梦想是“和大鼻子说说话”,这一愿望在震泽中学得以实现。学校从初一就开设了英语课,愿望的驱使,让我每一课都认真听讲,每一个单词都倒背如流。我被选为班里的英语课代表,上下课,我总是骄傲而嘹亮地喊“STAND UP”“SIT DOWN”,还带领同学唱英语歌。1963年高考填志愿,我征求班主任金本中老师的意见时,他几乎是脱口而出,“你填个‘北京外国语学院’吧。”
正是震泽中学培育了我学英语的“底气”,让我来到了北京,来到梦寐以求的大学。回忆起这些,我总忘不了母校,忘不了震泽中学,忘不了震泽中学的那些老师和他们身上平凡而又不寻常的故事。我想,一辈子做好一件平凡的事,那就是伟大吧!